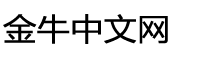上品寒士-第46部分(2/2)
作者:soweibo
,代有其人。
若说休沐日的司徒府是名流荟萃之所,那么每月十四乌衣巷谢家清谈雅集则聚集了江左年轻一辈高门子弟,这些高门子弟年轻气盛,辩论之激烈犹胜司徒府的聚会,两年来数十场辩难,各种论题,精彩纷呈,琅琊王氏的王凝之、王徽之兄弟、太原王氏的王爽、高平郗氏的郗恢(郗恢乃郗昙之子、郗超从弟、郗道茂的胞兄)、颖川庾氏的庾璟、陈郡袁氏的袁通、琅琊诸葛氏的诸葛曾、颖川荀氏的荀念,还有太原温氏、陈留蔡氏、汝南周氏子弟,这些青年俊杰摆动着麈尾、玉如意,各逞口舌之利,却无人能在老庄玄谈上折服谢道韫,也就无人敢娶谢道韫,有那善谑者笑言,除非王弼、夏侯玄复生,否则无人能娶谢氏女,再或者支公还俗,或能胜过谢道韫一筹——
谢府的清谈雅集名气越来越大,隐隐有超过司徒府之势,所谓助谈,就是从谢府兴起的,谢道韫与其弟谢玄联手,玄辩无敌,去年谢玄赴桓温西府任职,而谢朗、谢琰、谢韶不善清言,不能为堂姐助谈,所以谢道韫往往独自迎战四方玄辩之士,亦从未落下风——
乌衣巷并非街巷,而是前临清溪、后凭秦淮的一片形胜地,王、谢二族各占数顷,庭院深深、林园广大,温氏、乔氏、蔡氏这些大族也居住在这里。
陈操之一行沿秦淮河南岸往东行去,从绵延半里的琅琊王氏家族的宅第前经过,前面便是谢氏家族那土墙木构架的大宅,谢尚、谢奕、谢安、谢万的宅第依次排列,一遭土墙环绕,一个大门进出,显得家族很有凝聚力。
在谢府大院内的耳房前,停着六、七辆牛车,一个谢府管事和几名执役在门房接待,袁通袁子才是谢府常客了,虽屡屡被谢道韫驳得哑口无言,却就是喜欢来这里。
这时雨突然大起来,灯笼光照映下,密集的雨点如万箭攒射般落在青石板路上,雨雾溅起,迷蒙一层。
陈操之、顾恺之、袁通、支法寒便立在门房宽廊下等候骤雨稍歇,不然的话,虽然有雨具这么大的雨走到谢府正厅也会袜履尽湿。
yuedu_text_c();
袁通问那谢府管事:“诸葛永民到了没有?”
诸葛永民便是诸葛曾,已故尚书右仆射诸葛恢之孙,其先祖乃是东吴重臣诸葛瑾,诸葛瑾之弟便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南渡之前,琅琊诸葛氏的门第犹胜王、谢,南渡后略显衰微,这个诸葛曾也是谢府常客,颇有非谢道韫不娶的架势。
管事答道:“诸葛公子也是刚到,正在厅中与我家万石公相谈。”
袁通又问:“诸葛永民请来的助谈者是谁?”
管事道:“是范刺史之子范宁范武子。”
袁通吃了一惊:“竟然是范武子,范武子怎么会来此!”
陈操之心想:“谢万石还健在啊,史载谢万石兵败淮北之后,次年便郁郁而终,现在看来英台兄未嫁,谢万石也未死,历史已悄然改变。”轻声问顾恺之:“长康,范武子何人?”
顾恺之道:“就是前徐、兖二州刺史范汪之子范宁,范汪北伐失期,被桓温表奏朝廷贬为庶人,范氏衰微,但其子范宁范武子却是声名渐显,范宁好儒学,性质直,精于春秋三传,痛恨黄老之学,曾说王弼、何宴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此为迷众之大罪,其罪更深于桀、纣——”
陈操之奇道:“此人既对玄学清谈如此深恶痛绝,为何会来为诸葛永民助谈?”
顾恺之笑道:“南阳范氏与琅琊诸葛氏是世交,诸葛永民请出范武子也不稀奇,这个范武子虽痛恨正始玄风,却是对老庄之学下了很大苦功的,所谓深入浅出,要驳倒老庄玄学,首先必须对老庄玄学有通透的了解,这叫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传闻其不谈则已,谈起来一鸣惊人——”
那边支法寒与袁通低声商议了几句,袁通过来朝陈操之作揖道:“子重兄,在下想请子重兄助谈,还望子重兄鼎力相助。”
陈操之道墨眉一挑,看了支法寒一眼,说道:“有法寒师兄在此,我如何越俎代庖!”
支法寒上前道:“惭愧,范武子之玄辩非小僧所能屈,去年范武子曾至东安寺与吾师辩《庄子逍遥游》,范武子持‘万物各适其性即为逍遥’之论,妙理清通,吾师与之反复辩难,竟不能屈之——”
袁通惊道:“竟有这等事?范武子之玄辩竟连支公都不能屈之,那他岂不是江左年轻一辈第一人了!”
支法寒道:“范武子痛恨清谈,是以要在清谈上折服他人,据闻当世玄言诗宗孙绰孙兴公与范武子辩难终日,竟为范武子所屈,范武子还妄图挫败吾师,虽未如他愿,但其玄辩恐非小僧所能胜之,敢请陈檀越相助。”
陈操之敬谢不敏道:“在下虽曾研究过玄理,但甚少与人辩难,言讷口拙,恐负子才兄所托。”
袁通与陈操之只是初次见面,未领教过陈操之的才艺,对这个轰动全城的美男子嫉妒多于敬佩,担心陈操之徒有其表、华而不实,只因是支法寒力荐,所以袁通才来请陈操之助谈,现在听陈操之说,便道:“那好,还是法寒师兄为我助谈吧。”
支法寒也未再谦辞,毕竟对于一个雅好清谈者而言,也是极渴望挑战强手的,若能理屈范武子,岂不是为师增光!
……
夜雨滂沱,屋顶的筒瓦响成一片,风雨声中,偶尔传出棋子敲楸枰的脆响。
谢道韫独坐西窗下,听着窗外骤雨声,纤长的手指拈起一枚黑子敲在棋枰上,端详了一会,又拈起一枚白子紧紧靠在先前那枚黑子左边,棋盘上有近百枚黑白棋子,犬牙交错、缠绕追击,无声的厮杀异常激烈——
这是三年前谢道韫与陈操之同路回钱唐、在小镇广埭客栈歇夜时下的那局棋,那夜也是大雨如注,那夜谢道韫第一次未敷粉与陈操之相见,可是陈操之似乎对她的素颜不觉有异。
自升平三年菊月与陈操之别后,谢道韫常能听到关于陈操之的传闻,陈母弃世、陈操之结庐守墓、斗垮褚俭、钱唐陈氏入士籍、王劭盛赞陈操之有夏侯玄、刘琨风范……当然,更多的是陈操之与陆葳蕤之间的传言,诸如陈、陆二人在吴郡时日日相见,相约终身厮守云云——
每每听到这些传言,谢道韫就微微而笑,心道:“陈操之在吴郡怎么可能日日与陆葳蕤相会!论起来,陈操之与我——和小遏相处的时日更久吧,白日里在草堂听讲,夜里时常弈棋清谈,那桃林送客曲真让人难忘啊,三魂七魄似有一魂魄永远的留在那里,不然为什么梦里会常常在那片桃林外踯躅徘徊?”
花梨木书案上,一叠十二卷书册,正是谢玄去年从钱唐带回的《老子新义》、《论语新解》、《音韵论》、《明圣湖论玄集》和《一卷冰雪文》,谢道韫摩挲这一卷卷陈操之亲笔书写、亲手装订的书册,想着陈操之结庐守墓、勤学不辍的情景,不禁心中感动,那草棚灯影,寒来暑往,麻衣少年手不释卷、笔不停书的身影似乎就在眼前——
这十二卷书册谢道韫已手抄了其中六卷,每日夜里抄写时,就感觉在与陈操之娓娓而谈,恍若回到了狮子山下桃林小筑,抄着抄着,谢道韫就肘支书案,手托腮颊,凝眸望着虚空,忽颦忽笑,出神久之。
两年来数十场的清谈辩难,固然是谢道韫应付叔父谢安石、谢万石逼婚的一个借口,其实也是谢道韫对吴郡桃林小筑与陈操之等人交往的美好时光的缅怀,然而,纵使辩难再激烈,也难觅当日她与遏弟联手与陈操之、徐邈辩难时的美妙感觉,那一场又一场喧闹的辩难却难遣内心深处的寂寞——
风雪之夕、雨露之朝,谢道韫不免会想:“我将这样终老吗?我能与陈操之终生为友吗?陈操之可知我坚持之苦?”
三日前,陈操之将入建康的消息也传至了谢府,颇悉道韫娘子心事的婢女柳絮把这事说给谢道韫听,并说陈操之是与陆夫人同道进京的——
谢道韫微笑道:“很好啊,陈子重苦尽甘来了。”
yuedu_text_c();
婢女柳絮道:“现在市坊哄传陈郎君之事,明日陈郎君进城,一定会很热闹,娘子要不要去观看?”
谢道韫哂笑道:“有什么好看的,难道要我丢个香囊给他!”
婢女柳絮望着谢道韫的脸色,轻声道:“只要娘子肯丢,陈郎君未必不领情,娘子哪里会及不上那陆家娘子呢?”
谢道韫神色一冷,淡淡道:“柳絮,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柳絮赶紧道:“是。”背过身叹了口气,心道:“娘子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陈操之进城那日,柳絮与另一个谢府婢女结伴去清溪门观看了,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想挤近点看都好费力,归来后柳絮对谢道韫说起,谢道韫含笑道:“乌衣巷距清溪门不远,那喧闹声在这边都能听到——嗯,那陈郎君容貌变化大不大?”
柳絮道:“变化不大,稍微消瘦了一些,依然那么俊美,应该说比以前更俊美了,身量高了不少,约有七尺四寸,比遏郎君还高一些,遏郎君是七尺三寸吧。”
谢道韫点点头,心道:“七尺四寸,那可比我高很多了,我是七尺一寸,三年前我就是七尺一寸,一直没长,也再长不了啦。”这样一想,不免有些惆怅,好像因为高矮有别,陈操之就离她很远似的。
柳絮心知道韫娘子虽然表面淡然,其实是很想知道陈郎君的事的,当下仔细描绘陈操之入城的情景,说有女子散花赠香囊、又有宵小之徒嫉妒江左卫玠陈操之俊美,想丢鸡子让陈操之难堪,却反被人丢鸡子……
“娘子——娘子——”
谢道韫“啊”的一声回过神来,指间拈着的一枚棋子掉落楸枰上。
“何事?”
“清谈即将开始,请娘子去正厅屏风后就座吧。”
谢道韫“嗯”了一声,一边收棋子回奁,一边问:“来了些什么人?”
小婢禀道:“琅邪诸葛曾公子、陈郡袁通公子、吴郡顾恺之公子——”
谢道韫听到“顾恺之”三字,心里就是一跳,隐隐期待,就听得那小婢继续说道:“——南阳范宁公子、东安寺的僧人支法寒,还有一个就是前日入城万人空巷争看的钱唐陈操之公子。”
第二章 白马非马
这乌衣巷陈操之肯定会来的,但谢道韫没想到陈操之这么快就会来,而且是来参加今夜的清谈雅集。
谢道韫心“怦怦”乱跳,心想:“子重不会不知道谢府的清谈雅集是为我择婿而设的吧,那他来干什么,他想与我辩难,折服我?”
一念及此,谢道韫脸就红得发烫,但她毕竟不是那种容易自我陶醉的女子,随即想到陈操之极有可能是诸葛曾或者袁通请来助谈的,这样一想,心里又难免有些羞恼,暗道:“我谢道韫不肯嫁,你陈操之来也没有用,子重,你就真以为你的玄辩清谈一定能胜过我?未必吧。”
那前来禀报的小婢见道韫娘子脸忽红忽白,神色也是又喜又恼,不敢多言,赶紧去找柳絮,柳絮是道韫娘子的贴身侍婢。
等到柳絮赶来,谢道韫已经准备停当,便一起经由听雨长廊去正厅,听雨长廊是一条“之”字形的长廊,连接数座庭院,长廊由竹节覆顶,下雨时声音清晰,小雨时好比跳珠溅玉,清脆可喜,大雨时则如山间瀑布飞流喧腾,急管繁弦,满耳都是雨声,另有一种喧嚣中的静。
但今夜谢道韫却无漫步廊下听雨的兴致,行步匆匆,手里还握着一卷《明圣湖论玄集》。
谢道韫带着侍婢柳絮从后门进入正厅侧室,帘幕低垂,与正厅相隔,听到四叔父谢万石与人絮絮而语,四叔父兵败寿春被贬为庶人,去年虽经桓温举荐复擢为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为皇帝的顾问,乃清贵显职,但四叔父已无心理政,基本上退出了朝廷权力中枢,心高气傲的四叔父从此消沉,醉心于玄言清谈,还曾想服五石散解忧,被她劝住——
谢道韫倾听了一会,没有听到陈操之说话声,便轻声道:“柳絮,你去禀知我四叔父,就说我已经来了。”
柳絮搴帘出去,就在这帘幕掀开落下的瞬间,谢道韫看到一个漆冠葛衫、挺然端坐的身影,唇边的笑意一如往日——
那柳絮刚一出去,又飞快地踅回来,眼睛睁得老大,急急地对谢道韫道:“娘子,那个陈郎君在这里,就是钱唐陈操之陈郎君。”
谢道韫神色不动道:“我知道了,你慌里慌张成何体统,快去禀报四叔父。”
柳絮诧异地看了谢道韫一眼,又出去了,来到谢万石面前施礼道:“四郎主,道韫娘子已经来了。”
身披鹤氅、手执铁如意的谢万朝侧室帘幕一望,然后环视厅中诸人,说道:“那么就先听诸葛贤侄与袁贤侄之间的辩难了,你们两位的助谈分别是谁?”
yuedu_text_c();
袁通道:“谢常侍,晚辈请的是便是支公的高徒支法寒。”
诸葛曾道:“晚辈请的是南阳范武子。”
支法寒与范宁方才都已向谢万见过礼,这时都是躬身致意。
谢万问顾恺之道:“顾家郎君呢?”
顾恺之忙道:“晚辈与陈子重是来聆听诸位俊彦高论的,并不参与辩难。”
隔帘的谢道韫听到这句话,心里微微一空,感着淡淡的惆怅。
正厅中的围屏已布好,谢万之子谢韶进来对谢道韫道:“元姐,围屏已设好,你坐于屏后听他们辩难吧。”
谢道韫名韬元,字道韫,以是谢韶以“元姐”相称呼。
谢道韫便出了侧室,一架六幅折叠式屏风将大厅隔出一个独立空间,一朵一案一蒲团,谢道韫在蒲团上跪坐着,有侍女斟上清茶。
陈操之眼望围屏,那围屏上的画似乎是谢道韫所绘,有剡溪戴安道的画风,画的是会稽东山图,围屏后有灯光,那映在画屏上的清瘦的倩影就是英台兄吧,隐约可辨是女子髻钗,不复纶巾襦衫装束。
这时,袁通与支法寒一方,诸葛曾与范宁一方的辩难开始,双方各出一题,袁通先出题,出的是支法寒研究甚深的“白马非马论”。
“白马非马”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公孙龙的有趣的论题,公孙龙是刑名家的代表人物,所谓刑名家,就是以正名辩义、善于语言分析的辩者,而且往往是诡辩者,“白马非马”就是一个著名的诡辩逻辑——
当时赵国一带马瘟,大批战马死亡,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日,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到:“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讲:“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
公孙龙乃雄辩名士,这时自然要显示辩才,说道:“‘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者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给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非马。”
关吏越听越糊涂,被公孙龙这一通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和白马都过关去了——
支法寒好辩,熟读《战国策》,对张仪、苏秦、公孙龙、惠施的学说用功颇勤,这回以“白马非马”来辩难可谓是有备而来,而且昨夜在袁府与袁通长谈过,袁通对“白马非法论”相关问难也了如指掌,这时侃侃道来,雄辩滔滔,反观诸葛曾,哪里有半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潇洒,瞠目结舌,只等其助谈范宁范武子为他解围——
这场辩难其实是支法寒与范武子之间的辩难,两个主辩是傀儡。
范武子今年二十四岁,蓄有胡须,身量中等,容貌俊雅,但表情严肃,眉头总是微微蹙着,听袁通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一会,说得口干舌燥,住口饮茶,乃问:“子才兄对于‘白马非马’还有未尽之言
若说休沐日的司徒府是名流荟萃之所,那么每月十四乌衣巷谢家清谈雅集则聚集了江左年轻一辈高门子弟,这些高门子弟年轻气盛,辩论之激烈犹胜司徒府的聚会,两年来数十场辩难,各种论题,精彩纷呈,琅琊王氏的王凝之、王徽之兄弟、太原王氏的王爽、高平郗氏的郗恢(郗恢乃郗昙之子、郗超从弟、郗道茂的胞兄)、颖川庾氏的庾璟、陈郡袁氏的袁通、琅琊诸葛氏的诸葛曾、颖川荀氏的荀念,还有太原温氏、陈留蔡氏、汝南周氏子弟,这些青年俊杰摆动着麈尾、玉如意,各逞口舌之利,却无人能在老庄玄谈上折服谢道韫,也就无人敢娶谢道韫,有那善谑者笑言,除非王弼、夏侯玄复生,否则无人能娶谢氏女,再或者支公还俗,或能胜过谢道韫一筹——
谢府的清谈雅集名气越来越大,隐隐有超过司徒府之势,所谓助谈,就是从谢府兴起的,谢道韫与其弟谢玄联手,玄辩无敌,去年谢玄赴桓温西府任职,而谢朗、谢琰、谢韶不善清言,不能为堂姐助谈,所以谢道韫往往独自迎战四方玄辩之士,亦从未落下风——
乌衣巷并非街巷,而是前临清溪、后凭秦淮的一片形胜地,王、谢二族各占数顷,庭院深深、林园广大,温氏、乔氏、蔡氏这些大族也居住在这里。
陈操之一行沿秦淮河南岸往东行去,从绵延半里的琅琊王氏家族的宅第前经过,前面便是谢氏家族那土墙木构架的大宅,谢尚、谢奕、谢安、谢万的宅第依次排列,一遭土墙环绕,一个大门进出,显得家族很有凝聚力。
在谢府大院内的耳房前,停着六、七辆牛车,一个谢府管事和几名执役在门房接待,袁通袁子才是谢府常客了,虽屡屡被谢道韫驳得哑口无言,却就是喜欢来这里。
这时雨突然大起来,灯笼光照映下,密集的雨点如万箭攒射般落在青石板路上,雨雾溅起,迷蒙一层。
陈操之、顾恺之、袁通、支法寒便立在门房宽廊下等候骤雨稍歇,不然的话,虽然有雨具这么大的雨走到谢府正厅也会袜履尽湿。
yuedu_text_c();
袁通问那谢府管事:“诸葛永民到了没有?”
诸葛永民便是诸葛曾,已故尚书右仆射诸葛恢之孙,其先祖乃是东吴重臣诸葛瑾,诸葛瑾之弟便是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南渡之前,琅琊诸葛氏的门第犹胜王、谢,南渡后略显衰微,这个诸葛曾也是谢府常客,颇有非谢道韫不娶的架势。
管事答道:“诸葛公子也是刚到,正在厅中与我家万石公相谈。”
袁通又问:“诸葛永民请来的助谈者是谁?”
管事道:“是范刺史之子范宁范武子。”
袁通吃了一惊:“竟然是范武子,范武子怎么会来此!”
陈操之心想:“谢万石还健在啊,史载谢万石兵败淮北之后,次年便郁郁而终,现在看来英台兄未嫁,谢万石也未死,历史已悄然改变。”轻声问顾恺之:“长康,范武子何人?”
顾恺之道:“就是前徐、兖二州刺史范汪之子范宁,范汪北伐失期,被桓温表奏朝廷贬为庶人,范氏衰微,但其子范宁范武子却是声名渐显,范宁好儒学,性质直,精于春秋三传,痛恨黄老之学,曾说王弼、何宴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缙绅之徒翻然改辙,以至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遗风余俗,至今为患,此为迷众之大罪,其罪更深于桀、纣——”
陈操之奇道:“此人既对玄学清谈如此深恶痛绝,为何会来为诸葛永民助谈?”
顾恺之笑道:“南阳范氏与琅琊诸葛氏是世交,诸葛永民请出范武子也不稀奇,这个范武子虽痛恨正始玄风,却是对老庄之学下了很大苦功的,所谓深入浅出,要驳倒老庄玄学,首先必须对老庄玄学有通透的了解,这叫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传闻其不谈则已,谈起来一鸣惊人——”
那边支法寒与袁通低声商议了几句,袁通过来朝陈操之作揖道:“子重兄,在下想请子重兄助谈,还望子重兄鼎力相助。”
陈操之道墨眉一挑,看了支法寒一眼,说道:“有法寒师兄在此,我如何越俎代庖!”
支法寒上前道:“惭愧,范武子之玄辩非小僧所能屈,去年范武子曾至东安寺与吾师辩《庄子逍遥游》,范武子持‘万物各适其性即为逍遥’之论,妙理清通,吾师与之反复辩难,竟不能屈之——”
袁通惊道:“竟有这等事?范武子之玄辩竟连支公都不能屈之,那他岂不是江左年轻一辈第一人了!”
支法寒道:“范武子痛恨清谈,是以要在清谈上折服他人,据闻当世玄言诗宗孙绰孙兴公与范武子辩难终日,竟为范武子所屈,范武子还妄图挫败吾师,虽未如他愿,但其玄辩恐非小僧所能胜之,敢请陈檀越相助。”
陈操之敬谢不敏道:“在下虽曾研究过玄理,但甚少与人辩难,言讷口拙,恐负子才兄所托。”
袁通与陈操之只是初次见面,未领教过陈操之的才艺,对这个轰动全城的美男子嫉妒多于敬佩,担心陈操之徒有其表、华而不实,只因是支法寒力荐,所以袁通才来请陈操之助谈,现在听陈操之说,便道:“那好,还是法寒师兄为我助谈吧。”
支法寒也未再谦辞,毕竟对于一个雅好清谈者而言,也是极渴望挑战强手的,若能理屈范武子,岂不是为师增光!
……
夜雨滂沱,屋顶的筒瓦响成一片,风雨声中,偶尔传出棋子敲楸枰的脆响。
谢道韫独坐西窗下,听着窗外骤雨声,纤长的手指拈起一枚黑子敲在棋枰上,端详了一会,又拈起一枚白子紧紧靠在先前那枚黑子左边,棋盘上有近百枚黑白棋子,犬牙交错、缠绕追击,无声的厮杀异常激烈——
这是三年前谢道韫与陈操之同路回钱唐、在小镇广埭客栈歇夜时下的那局棋,那夜也是大雨如注,那夜谢道韫第一次未敷粉与陈操之相见,可是陈操之似乎对她的素颜不觉有异。
自升平三年菊月与陈操之别后,谢道韫常能听到关于陈操之的传闻,陈母弃世、陈操之结庐守墓、斗垮褚俭、钱唐陈氏入士籍、王劭盛赞陈操之有夏侯玄、刘琨风范……当然,更多的是陈操之与陆葳蕤之间的传言,诸如陈、陆二人在吴郡时日日相见,相约终身厮守云云——
每每听到这些传言,谢道韫就微微而笑,心道:“陈操之在吴郡怎么可能日日与陆葳蕤相会!论起来,陈操之与我——和小遏相处的时日更久吧,白日里在草堂听讲,夜里时常弈棋清谈,那桃林送客曲真让人难忘啊,三魂七魄似有一魂魄永远的留在那里,不然为什么梦里会常常在那片桃林外踯躅徘徊?”
花梨木书案上,一叠十二卷书册,正是谢玄去年从钱唐带回的《老子新义》、《论语新解》、《音韵论》、《明圣湖论玄集》和《一卷冰雪文》,谢道韫摩挲这一卷卷陈操之亲笔书写、亲手装订的书册,想着陈操之结庐守墓、勤学不辍的情景,不禁心中感动,那草棚灯影,寒来暑往,麻衣少年手不释卷、笔不停书的身影似乎就在眼前——
这十二卷书册谢道韫已手抄了其中六卷,每日夜里抄写时,就感觉在与陈操之娓娓而谈,恍若回到了狮子山下桃林小筑,抄着抄着,谢道韫就肘支书案,手托腮颊,凝眸望着虚空,忽颦忽笑,出神久之。
两年来数十场的清谈辩难,固然是谢道韫应付叔父谢安石、谢万石逼婚的一个借口,其实也是谢道韫对吴郡桃林小筑与陈操之等人交往的美好时光的缅怀,然而,纵使辩难再激烈,也难觅当日她与遏弟联手与陈操之、徐邈辩难时的美妙感觉,那一场又一场喧闹的辩难却难遣内心深处的寂寞——
风雪之夕、雨露之朝,谢道韫不免会想:“我将这样终老吗?我能与陈操之终生为友吗?陈操之可知我坚持之苦?”
三日前,陈操之将入建康的消息也传至了谢府,颇悉道韫娘子心事的婢女柳絮把这事说给谢道韫听,并说陈操之是与陆夫人同道进京的——
谢道韫微笑道:“很好啊,陈子重苦尽甘来了。”
yuedu_text_c();
婢女柳絮道:“现在市坊哄传陈郎君之事,明日陈郎君进城,一定会很热闹,娘子要不要去观看?”
谢道韫哂笑道:“有什么好看的,难道要我丢个香囊给他!”
婢女柳絮望着谢道韫的脸色,轻声道:“只要娘子肯丢,陈郎君未必不领情,娘子哪里会及不上那陆家娘子呢?”
谢道韫神色一冷,淡淡道:“柳絮,不许再说这样的话。”
柳絮赶紧道:“是。”背过身叹了口气,心道:“娘子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陈操之进城那日,柳絮与另一个谢府婢女结伴去清溪门观看了,真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想挤近点看都好费力,归来后柳絮对谢道韫说起,谢道韫含笑道:“乌衣巷距清溪门不远,那喧闹声在这边都能听到——嗯,那陈郎君容貌变化大不大?”
柳絮道:“变化不大,稍微消瘦了一些,依然那么俊美,应该说比以前更俊美了,身量高了不少,约有七尺四寸,比遏郎君还高一些,遏郎君是七尺三寸吧。”
谢道韫点点头,心道:“七尺四寸,那可比我高很多了,我是七尺一寸,三年前我就是七尺一寸,一直没长,也再长不了啦。”这样一想,不免有些惆怅,好像因为高矮有别,陈操之就离她很远似的。
柳絮心知道韫娘子虽然表面淡然,其实是很想知道陈郎君的事的,当下仔细描绘陈操之入城的情景,说有女子散花赠香囊、又有宵小之徒嫉妒江左卫玠陈操之俊美,想丢鸡子让陈操之难堪,却反被人丢鸡子……
“娘子——娘子——”
谢道韫“啊”的一声回过神来,指间拈着的一枚棋子掉落楸枰上。
“何事?”
“清谈即将开始,请娘子去正厅屏风后就座吧。”
谢道韫“嗯”了一声,一边收棋子回奁,一边问:“来了些什么人?”
小婢禀道:“琅邪诸葛曾公子、陈郡袁通公子、吴郡顾恺之公子——”
谢道韫听到“顾恺之”三字,心里就是一跳,隐隐期待,就听得那小婢继续说道:“——南阳范宁公子、东安寺的僧人支法寒,还有一个就是前日入城万人空巷争看的钱唐陈操之公子。”
第二章 白马非马
这乌衣巷陈操之肯定会来的,但谢道韫没想到陈操之这么快就会来,而且是来参加今夜的清谈雅集。
谢道韫心“怦怦”乱跳,心想:“子重不会不知道谢府的清谈雅集是为我择婿而设的吧,那他来干什么,他想与我辩难,折服我?”
一念及此,谢道韫脸就红得发烫,但她毕竟不是那种容易自我陶醉的女子,随即想到陈操之极有可能是诸葛曾或者袁通请来助谈的,这样一想,心里又难免有些羞恼,暗道:“我谢道韫不肯嫁,你陈操之来也没有用,子重,你就真以为你的玄辩清谈一定能胜过我?未必吧。”
那前来禀报的小婢见道韫娘子脸忽红忽白,神色也是又喜又恼,不敢多言,赶紧去找柳絮,柳絮是道韫娘子的贴身侍婢。
等到柳絮赶来,谢道韫已经准备停当,便一起经由听雨长廊去正厅,听雨长廊是一条“之”字形的长廊,连接数座庭院,长廊由竹节覆顶,下雨时声音清晰,小雨时好比跳珠溅玉,清脆可喜,大雨时则如山间瀑布飞流喧腾,急管繁弦,满耳都是雨声,另有一种喧嚣中的静。
但今夜谢道韫却无漫步廊下听雨的兴致,行步匆匆,手里还握着一卷《明圣湖论玄集》。
谢道韫带着侍婢柳絮从后门进入正厅侧室,帘幕低垂,与正厅相隔,听到四叔父谢万石与人絮絮而语,四叔父兵败寿春被贬为庶人,去年虽经桓温举荐复擢为散骑常侍,散骑常侍为皇帝的顾问,乃清贵显职,但四叔父已无心理政,基本上退出了朝廷权力中枢,心高气傲的四叔父从此消沉,醉心于玄言清谈,还曾想服五石散解忧,被她劝住——
谢道韫倾听了一会,没有听到陈操之说话声,便轻声道:“柳絮,你去禀知我四叔父,就说我已经来了。”
柳絮搴帘出去,就在这帘幕掀开落下的瞬间,谢道韫看到一个漆冠葛衫、挺然端坐的身影,唇边的笑意一如往日——
那柳絮刚一出去,又飞快地踅回来,眼睛睁得老大,急急地对谢道韫道:“娘子,那个陈郎君在这里,就是钱唐陈操之陈郎君。”
谢道韫神色不动道:“我知道了,你慌里慌张成何体统,快去禀报四叔父。”
柳絮诧异地看了谢道韫一眼,又出去了,来到谢万石面前施礼道:“四郎主,道韫娘子已经来了。”
身披鹤氅、手执铁如意的谢万朝侧室帘幕一望,然后环视厅中诸人,说道:“那么就先听诸葛贤侄与袁贤侄之间的辩难了,你们两位的助谈分别是谁?”
yuedu_text_c();
袁通道:“谢常侍,晚辈请的是便是支公的高徒支法寒。”
诸葛曾道:“晚辈请的是南阳范武子。”
支法寒与范宁方才都已向谢万见过礼,这时都是躬身致意。
谢万问顾恺之道:“顾家郎君呢?”
顾恺之忙道:“晚辈与陈子重是来聆听诸位俊彦高论的,并不参与辩难。”
隔帘的谢道韫听到这句话,心里微微一空,感着淡淡的惆怅。
正厅中的围屏已布好,谢万之子谢韶进来对谢道韫道:“元姐,围屏已设好,你坐于屏后听他们辩难吧。”
谢道韫名韬元,字道韫,以是谢韶以“元姐”相称呼。
谢道韫便出了侧室,一架六幅折叠式屏风将大厅隔出一个独立空间,一朵一案一蒲团,谢道韫在蒲团上跪坐着,有侍女斟上清茶。
陈操之眼望围屏,那围屏上的画似乎是谢道韫所绘,有剡溪戴安道的画风,画的是会稽东山图,围屏后有灯光,那映在画屏上的清瘦的倩影就是英台兄吧,隐约可辨是女子髻钗,不复纶巾襦衫装束。
这时,袁通与支法寒一方,诸葛曾与范宁一方的辩难开始,双方各出一题,袁通先出题,出的是支法寒研究甚深的“白马非马论”。
“白马非马”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公孙龙的有趣的论题,公孙龙是刑名家的代表人物,所谓刑名家,就是以正名辩义、善于语言分析的辩者,而且往往是诡辩者,“白马非马”就是一个著名的诡辩逻辑——
当时赵国一带马瘟,大批战马死亡,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这日,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到:“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讲:“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
公孙龙乃雄辩名士,这时自然要显示辩才,说道:“‘马’是指名称而言,‘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者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给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所以说白马非马。”
关吏越听越糊涂,被公孙龙这一通高谈阔论搅得晕头转向,如坠云里雾中,不知该如何对答,无奈只好让公孙龙和白马都过关去了——
支法寒好辩,熟读《战国策》,对张仪、苏秦、公孙龙、惠施的学说用功颇勤,这回以“白马非马”来辩难可谓是有备而来,而且昨夜在袁府与袁通长谈过,袁通对“白马非法论”相关问难也了如指掌,这时侃侃道来,雄辩滔滔,反观诸葛曾,哪里有半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潇洒,瞠目结舌,只等其助谈范宁范武子为他解围——
这场辩难其实是支法寒与范武子之间的辩难,两个主辩是傀儡。
范武子今年二十四岁,蓄有胡须,身量中等,容貌俊雅,但表情严肃,眉头总是微微蹙着,听袁通滔滔不绝地说了好一会,说得口干舌燥,住口饮茶,乃问:“子才兄对于‘白马非马’还有未尽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