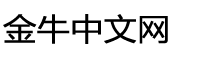天下春秋第82部分阅读(2/2)
作者:未知
兵伐蔡,入蔡都,蔡侯肉袒伏罪,尽出宝藏美玉,楚师方退。楚文王将所得宝货尽赐桃花夫人,以致楚国上下不悦,以为士卒在前拼命,所得却归一妇人,怨王之甚,以致后来楚文王与巴人交战,楚人有内应不说,士卒又不肯用力,楚文王战败而死。”
众人“噢”了一声,心忖这楚文王一心为了桃花夫人,虽然难得,却因女色而轻士卒,以致败亡,也是自寻其祸。
老者续道:“楚文王死后,桃花夫人长子嗣位,但这人只继了楚文王的酒色,但其父的武略丝毫也没有学到,在位三年,专事游猎,无一政施设,故而谥不称王,只称‘堵敖’。桃花夫人次子熊恽文才武略俱佳,向为桃花夫人所爱,又为国人推服。堵敖心忌其弟,常想杀之,左右多有为熊恽周旋者,以致反复不决。熊恽自不能免,索性暗蓄死士,乘堵敖出猎时袭而杀之,以病薨告知桃花夫人,桃花夫人心中虽疑,也不欲明白此事,否则仅余一子也难免,遂使诸大夫立熊恽为王,即楚成王是也。”
伍封道:“楚成王用子文为令尹,灭弦、黄、六、英、夔,楚境四扩,武攻强盛一时。”
老者道:“楚成王初立,以王叔子元为令尹。子元自其兄楚文王死后,常有篡立之心,又慕其嫂桃花夫人之美,欺楚成王年少,遂于王宫之旁大筑馆舍,每日歌舞奏乐,欲惑桃花夫人之心。桃花夫人听说是令尹子元的新馆,叹道:‘先王舞干戈以习武事,以征诸侯,是以四方朝贡不绝。如今令尹不图武事,而乐舞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侍卫将桃花夫人之语转告子元,子元甚感惭愧,遂发兵车六百乘,亲自引着伐郑,但郑国防守甚严,子元无甚兵略,见无机可乘,连夜退兵。他不战而退,反让人先到桃花夫人处谎称得胜。桃花夫人怎会被人所骗?道:‘令尹大获全胜,当宣示国人,哪有这么鬼鬼祟祟跑到未亡人之处相告的?’子元大为惭愧。”
楚月儿笑道:“桃花夫人聪明得紧。子元想必会收敛心神,专心国事了吧?”
那老者摇了摇头,续道:“子元伐郑无功,内不自安,又想成了楚王,桃花夫人自然为他所得,是以篡谋甚急。后来桃花夫人略有小恙,子元假称问安,移寝具入宫,桃花夫人却使侍女执剑守户,子元不敢闯入,留在宫中三日不出,纠缠不休,让其家勇数百围住王宫。桃花夫人派人向子文告急,子文密奏楚成王,半夜袭破子元家勇,入宫杀了子元。到桃花夫人寝室前问安。次日楚成王升殿,灭了子元一家,其后才用子文为令尹,国事定而大治。桃花夫人故后,楚成王葬母于父冢,此地息侯所葬之处,楚成王遵母之嘱,在此处雕了这座桃花夫人之像,以慰息侯于九泉之下。”
伍封“嘿”了一声,赞道:“这桃花夫人其实不仅貌美,还通达明断,了不起!”楚月儿笑嘻嘻地道:“女子通达明断者不少,但美貌而通达明断者甚少,怪不得夫君赞她!”伍封笑道:“怎么月儿也学起公主的脾气来,总当为夫是个好色之徒?”想起妙公主的诸般顽皮,不禁微笑,心忖自己似乎也是个好色之徒,道:“我若见了桃花夫人,自然不会如子元之不堪,不过楚文王为一女而大兴杀伐,我未必做不出来。譬如田相若将月儿索要回去,我定会杀入田府以夺回来,诸事不顾。”
楚月儿格格笑道:“夫君多半做得出来,正如夫君所说,你这番狠劲也是非同小可!”伍封哈哈大笑,道:“哈哈,是么?”
众人听了这半天故事,甚有感触,伍封让鲍兴拿了五金给这老者,这五金即是百两黄金,老者推辞道:“老夫只是说几句话,何用如此厚赐?”
伍封笑道:“老先生这故事说得好听,足解在下等旅途之困乏,区区五金不算什么。”老者摇头道:“黄金之物老夫身上多得是,并无所用。”他说着话,随手从袖中拿出一把楚国常用的饼金来,放在地上,又从怀中摸了一把,赫然是数块宝玉。
众人想不到这老者随身携有许多金玉,心想他的大袖之内不知还有多少。楚月儿好奇道:“老先生原来十分富阔,夫君可看走眼了。”伍封道:“老先生谈吐非凡,想必是大有身份之人,未知能否相告名讳?”
老者微笑道:“老夫是扁鹊的弟子东皋公,与令尊曾有一面之缘。”伍封大惊,叩拜道:“原来是先父之大恩人,晚辈失敬了。”楚月儿等人也忙跪叩。
东皋公将伍封搀起来,又让楚月儿等人起身,道:“老夫是个闲散小人,隐居于此地久矣,龙伯和月公主如此大礼,老夫可担当不起,恐致折寿。老夫活了九十四岁,还想多活几年。”
这东皋公的确是伍子胥的恩人。当年伍子胥携公子胜(白公胜)东逃往吴,路过昭关,关上有楚兵把守,悬图刻形貌,无法通过,伍子胥大急之下,一夜白发。幸好他在关内林中遇到东皋公,东皋公见伍子胥身高一丈,形容极伟,遂请友人皇甫讷假扮伍子胥,皇甫讷身高九尺,又与伍子胥有些相像,东皋公用些药汤将伍子胥面容变色,取村家衣服给伍子胥和公子胜换上。黎明之时,皇甫讷故意慌慌张张地过关,被士卒当成伍子胥拿住,叫嚷吵闹之下,伍子胥和公子胜便混过了昭关。他头白变白,脸上易色,故意弯腰以掩其高,遂能过关。伍子胥过关许久,东皋公才拿着过关文牒到关上来,声称与皇甫讷相约过关东游,楚人验实,才知道捉错了人,陪罪放了,坚守昭关如故,却不知道伍子胥早已经混过了关去。
伍封向众人说起此事,道:“若非老先生援手,家父早晚亡于楚国,我也就生不出来了。是以老先生对我们一家有天大恩德。”
东皋公摇头道:“老夫倒不投你们报恩,老夫一生救人,从不杀人,只是见令尊是当世英雄,不忍他含冤而亡,才会偶施援手。今日老夫路过此地,被龙伯的从人请来,老夫恰好知道桃花夫人之事,才会向你们说一会儿话。”
伍封道:“先父多年来派人寻觅老先生和皇甫先生,可一直未能找到,未知皇甫先生在何处,晚辈想向他叩头致谢。”
东皋公摇头道:“十余年前,皇甫老弟入山采药,误入金夜花丛,中了花毒,老夫一时间寻不到解此毒之药,三日后皇甫老弟便死了。”
伍封叹了口气,觉得甚为遗憾。楚月儿点头道:“金夜花夜间开光,发金色之光,白昼看时,与寻常牵牛花相似。要解此毒,除了防风、甘草、桂枝之外,非得用一味雪昼草不可。此草在极北之地才有,楚国可寻不着。怪不得以老先生之能,也不能救到皇甫先生。”
东皋公大奇,惊道:“咦,原来月公主也懂得医道。虽数十年的医士也不易知道这雪昼草、金夜花,月公主竟能知道这两种奇物,解法也得当,委实高明!”
楚月儿笑道:“月儿可不知道,这是计然的竹简上写的,月儿记在心中,也不知道对不对。”
东皋公问道:“计然是个什么人?”楚月儿将计然之事简单说了一遍,道:“他那竹简月儿记在心中,可惜放在莱夷未曾带来。”
东皋公大感兴趣,道:“原来世上还有人专研用毒解毒之法,听来高明之极。既然你记得,大可以一一说给老夫听。”
楚月儿道:“是。譬如说用锡配天仙子,便可合成一味毒药,名叫‘惜见天’,此毒夜发,天光即死,要解此毒,便得用杏仁、黑豆、甘草,再用蓝子汁和盐水煮成药汤,便可以解毒了。”东皋公闭目沉吟,不住点头,道:“高明,高明。这一味盐水想得周到,老夫一时间便想不出来,不过若将蓝子汁改为绿豆汁,只怕更有解毒之效。”他是扁鹊的亲传弟子,医术自然要较计然高,楚月儿深信不疑,道:“简中有几种毒药都用绿豆以解,这绿豆汁自然是好。还有一毒,是用天南星配芫花、巴豆,三毒相合,十分厉害,要解此毒……”,东皋公沉吟道:“这三种都是剧毒之药,老夫若用生姜、黑豆混碾成粉,再加上大豆汁、黄莲汁、菖蒲水,以冷水调合服用,理应可解这三毒。”楚月儿点头道:“简上确是这么用法,不过多了一种干姜汁。”东皋公猛拍大腿道:“妙!这干姜汁用得极妙!药量如何?”楚月儿道:“常人用当然是生姜一两三钱、黑豆四两,大豆等各用五钱轧汁;若是肥胖之人,须得加些……”
他们一老一少说得十分高兴,伍封等人面面相觑,忍不住暗暗好笑,不敢打扰。楚月儿和东皋公越说越是兴奋,说了好一阵,东皋公睁眼道:“是了,老夫扯着月公主这么长篇大论,不免耽误了你们的行程。”
伍封忙道:“无妨,我们并无急事,大可以在此地设帐过夜。”东皋公笑道:“这如何使得?不如这么着,老夫随你们一路前往,途中正好于月公主研究些医术,一举两得。老夫许久未闻过高明的用药之术了。”
伍封道:“晚辈正有意请老先生到我成周的府上小住,同行更好。老先生是否还有家人?晚辈派人一并接来。”东皋公笑道:“老夫只身一人,行至何处便在何处落脚,何来家人?”
鲍兴将地上饼金捡起来交给东皋公,伍封命将铜车华盖上的锦帐放下来,楚月儿扶了东皋公上铜车安座,人车前行,东皋公却与楚月儿在铜车帐中滔滔不绝。便听东皋公道:“月公主,这……”,楚月儿道:“老先生唤我‘月儿’便是。”东皋公道:“是极,月儿,有一种蛇毒可十分厉害,名为乌头子,喜欢在川乌、草乌附近藏身,竹简上可有解法么?”楚月儿道:“似未见过解法,不过简上说蛇所在处,七步之内必有解药,那川乌、草乌是否可为解药?不过川乌有剧毒,可不敢用。”东皋公呵呵笑道:“正是用川乌来解,这叫作以毒攻毒。用草乌也可解之,不过川乌草乌不过混用,单用一味即可。”楚月儿问道:“为何不能混用?”东皋公道:“川乌草乌相配大有禁忌,合用则失去药效,此类禁忌之药有十九种,叫‘十九畏’;还有十八种药不能混配,否则便有大毒,足以致命,称为‘十八反’。用药者不可不知,老夫教你这歌诀,日后你用药时要谨记,另外,药剂使用分君臣佐使,不可不知。先背这‘十九畏’,歌诀是:‘硫磺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
伍封心忖这二人一个是九十四岁的白首老翁,一个是十七八岁的美貌少女,偏能说到一起去,兴趣昂然,也算是奇事一件,觉得甚为有趣。
一路上有东皋公相随,行程就慢了许多,虽然这世上有很多人被称为神医,但真正的神医,无过于扁鹊者。东皋公是扁鹊的弟子,从医八十余年,医道非同小可,世上再无第二人可以比拟,这些天他将用药的诸般法门禁忌效用一一说给楚月儿听,又时时停车,带楚月儿在道旁采药辨认,楚月儿对此道本有兴趣,用心记忆不提。
这日到了棠溪,还离城邑甚远,便见夫概带了数人在道旁等着。
伍封微觉愕然,将楚月儿从铜车上唤出来,带众女下车拜见夫概,伍封道:“舅爷爷可好。”夫概笑道:“还好,难得封儿有心,竟绕到此地来探我。不过老夫无甚颜面见人,不敢迎你入城。”
圉公阳和庖丁刀将一早准备好的一车礼物拿上来,夫概身后转上来一人接过,看那人时,正是上次见过的那力气惊人的庄战。
伍封忽想起上次在吴国时,小鹿绕道楚国买梁种,再赶到吴国,说过途中遇到了这庄战,还比试过刀剑,连小鹿也不敌此人。后来匆匆回齐,一路上多生变故,叶柔亡故,众人心情寥落,回齐之后又忙着送田燕儿成亲,一直未细问过小鹿与庄战交手的事。此刻见到此人,兴趣大生,不住地向庄战打量。
众人在道旁林间席地而坐,伍封让鲍兴请东皋公来,东皋公却不愿意见生人,伍封只好由得他在车上休息。夫概的从人奉上美酒瓜果供众人解热,夫概见伍封和楚月儿都注意这庄战,笑道:“封儿,小战力气不小,剑术又精,老夫对他甚为看重。上次瞒着老夫与令徒小鹿比试了一次,被老夫好一顿责怪。”
楚月儿看了庄战好半天,甚觉亲近,忽想起渠公到她族中挑选人才之事,她和伍封在鲁国为孔子吊丧,渠公将庄大等人带了去,还说族中有一人名战,素为族人推重,这人之名也是“战”,莫非就是此人?她道:“夫君,渠公曾说我族人之中有一人善剑术,名为战。”
伍封也想了起来,夫概笑道:“月公主猜得不错,小战便是你的堂侄,他常回族中去,是以你们族人都知道他。”
庄战道:“其实在上次见面时,小人便依稀认出了月公主。虽然说女大十八变,月公主长得高了,也更为美丽,但眉心那颗美人痣小人是认得的。月公主四岁时,小人正好回族中去,还抱过月公主。只是月公主嫁了龙伯,身份尊贵,小人可不敢相认,免得别人当小人是否趋炎附势之徒。”
楚月儿又惊又喜,道:“月儿可没有什么印象。”伍封笑道:“若非月儿想起来,小战是否还不想相认呢?”寻思:“小战与月儿姊弟果然关系不同,庄氏老一辈都认不出月儿,偏偏小战能认出,若非他以前对她们姊妹细心照顾,怎能认识?”
庄战道:“眼下月公主是楚国公主,龙伯又是天子之师,小人再要相认,岂非更加不成样子?是以央师父不要说出我的身份来。”
伍封佩服道:“原来小战是舅爷爷的徒儿,怪不得剑术能胜过小鹿儿。”
夫概摇头道:“小战的剑术胜过老夫多矣,可不是老夫教的。他尊老夫为师,是因为我教他冶铁铸剑之技,不过他往吴越楚国寻访名师学习铸艺,比老夫的铸艺要高明不少。”
伍封奇道:“小战的剑术能胜过小鹿儿,非剑术高手绝对教不出来,未知师从何人?”
庄战摇头道:“小人这套剑术是小时候用一条两头蛇与人交换来的。”伍封与楚月儿大吃一惊:“两头蛇?”伍封道:“那人想必是剑中圣人支离益的门下。”
庄战道:“十余年前,小人在林中见到一条长长的两头蛇,不知其厉害,用竹竿按住,正想将蛇打死,忽然林中转出一个人来。那人并未说过名字,不过他气派甚大,虽然他可以轻松将蛇夺了去,却不愿意有失身份,便要出金帛买走。小人说此蛇见者不吉,非打死不可,他劝了小人好半天,见小人不要金帛玉器,遂说要传授小人一套剑术,以换此蛇。小人自小对剑术便很感兴趣,便答应了他,他先将蛇装入竹篓,然后教了小人一套剑术。名为‘开山剑术’,说小人的力气甚大,正合用这套剑术。”
伍封心想这“开山剑术”除了自己懂得一些外,便只有支离益和朱平漫二人擅长,董门其他的人包括董梧在内都不习此套剑术,问道:“那人多大年纪,是何模样?”
庄战道:“那时他有四十余岁,眼下应该五十多岁了,生得十分高大,约有九尺,模样古朴。”楚月儿摇头道:“不是朱平漫。”伍封道:“董梧这人没有这么高大,说不定这人便是支离益。”
庄战练剑这么久,自然知道支离益的大名,又惊又喜,道:“他是剑中圣人支离益?!他甚有耐心,教了小人一个时辰,小人练会之后,他又用了两个时辰与小人拆招,指点每一招的用法,小人慢慢使给他看,他长叹了一声,说他有一个弟子也会这剑术,不过日后小人这套剑术练熟了,必定胜过他的弟子。”
伍封和楚月儿知道那人口中的弟子必是朱平漫,一头,道:“那人果然是支离益。”伍封笑道:“小战能得剑中圣人支离益亲授剑术,福气可不小,怪不得能胜过小鹿儿。”楚月儿道:“以小战的天资,支离益怎会轻易放过,不收为弟子呢?”
庄战道:“他也曾说过要收徒,不过小人不愿意离开楚国,是以未拜他为师,他只好带了那两头蛇离去。”
伍封问道:“如此良师天下间只有支离益一人,你为何不愿意随他去?”
庄战叹道:“当时小人才八九岁,怎知道面前的是天下奇人?何况二十九年前小人才四岁,随家父离开了族中,正值吴军伐楚,攻入郢地,国内大乱,家父抱着小人兄弟二人正逢乱兵,被撞得跌倒了,人群拥动,小人便与父兄失散。小人常想,父兄早晚会来找小人,是以不敢离开楚国去。”
夫概道:“老夫从吴国逃出来奔楚,被封在棠溪,一路过来,在途中见到小战乞讨。小战年方五岁,却甚有胆气,老夫便将他捡了回来收养,过了七八年才打听到他族人的下落,命他回去,不过他回去之后又赶回堂溪,他怕父兄回族中去,其后每过两三年便回族中一次。”
伍封叹道:“我在月儿族中时,族长说其二弟离族而去,原来就是小战的父亲,这真是巧得很。”
楚月儿道:“夫君,好不好我们再来个千金悬赏,为小战寻觅父兄?”伍封点头道:“如此甚好,只要知道小战父兄名讳,便好办了。”
庄战喜道:“家父带小人出来时,以庄为姓,家父名叫庄城,家兄……”,伍封和楚月儿愕然道:“庄城?!”
庄战惊道:“怎么?”楚月儿道:“成周梦王姬府上总管便叫庄城。”他说起庄城的样貌,庄战大喜,道:“那正是家父,想不到他老人家在成周。”
伍封叹道:“我一生遇到过巧事不少,尤以今日算是巧之有巧。”楚月儿笑道:“幸亏夫君心思一动,要来探望舅爷爷,这才搞清楚许多事。”
夫概呵呵笑道:“虽然小战不愿意,但老夫听说大王赐封儿之子为庄氏之长,赏赐邑地,今日本就想让小战与你们相认,然后为你们效力,也免得埋没了小战的剑术。想不到还有如此变故,这真是难得。小战,你们便随封儿去吧,日后也好见功。”
庄战道:“这虽然是好,不过小人要问问家父的意思,这便随了龙伯和月公主去,先拜见父兄再说。”
伍封道:“如此甚好,令尊便会答应。”又皱起眉头,道:“小战,有一事你先得心中有数,令尊说其二子一女均已经亡故,想是当你已经亡于乱中。不过令兄只怕已经不在世上了,他有一子名曰庄周,随令尊在一起。想来是令兄与令尊在一起,长大后娶妻生子,早些年亡故。”
庄战怔了怔,眼中微微湿润,叹道:“其实小人心中早有了准备,只是不敢细想而已。”
夫概叹道:“伍氏一家与吴王有仇,幸亏封儿不记旧怨,以吴民和宗祀为重,两番败越,却被夫差加害,老夫也甚为有愧。小战自小随我长大,剑术也高,老让小战投于封儿府上,也算是报答封儿。如今小战已经得知父亲的下落,老夫的心愿已了。小战,你与封儿和月公主是亲人,今后当尽力报效,不可懈怠。”
庄战点头道:“如果家父愿意让小人投入龙伯府上,我便尽力而为。”伍封皱眉道:“小战怎不叫我们为姑姑、姑丈,非要称‘月公主’、‘龙伯’这么见外?”
庄战摇头道:“龙伯手下臣属众多,当着这么多人,自然当叫‘龙伯’、‘公主’,免得别人以为小人仗着是亲戚,打着你们的旗号来唬人。何况家父是月公主的父亲的堂侄,小人与月公主之间的亲戚关系可有些疏远了。”
楚月儿不悦道:“都是一族之人,亲疏哪用分得那么细?”庄战道:“家国都有其规矩,可不能乱套。眼下小人还不是龙伯和月公主的臣属,非得这么叫不可。”
伍封与楚月儿见他颇有些迂腐,苦笑摇头,心忖夫概并不怎么守礼,否则便不会有自立吴王之事,想不到他这弟子却将谦躬守礼之极。当下引庄战见过鲍兴等人,又让庄战回城收拾行囊。
众人谈了许久,等庄战拿了个小行囊来,楚月儿见他只身一人,问道:“小战还未成亲么?”庄战道:“未得家父之命,怎敢私下成亲?”
夫概怕耽误了伍封的路程,命从人将准备好的礼物拿上来,那是十口铁剑。夫概起身告辞,众人互道珍重,伍封一众带着庄战继续北上。
东皋公在车上苦候了楚月儿这么久,急不可耐,此刻楚月儿才上车,东皋公便道:“月儿,你可知有的毒药服上,从外表可看不出来,待外征象出来褒时,已经不能救了。你又用何法知道他是否中毒,所中何毒?”
楚月儿道:“这个月儿便不知道了。”东皋公笑道:“我告诉你这法子,医道所谓望闻问切,用此四法便知。老夫先教你这‘切’法,切分脉诊和触诊,脉诊即是切脉象,人之脉象常见的二十八种,如浮、沉、迟、缓等等,你看这腕上,此处曰‘寸’,此处曰‘关’,此处曰‘尺’,手指这么搭上去,便知……,咦!月儿,你这脉象古怪,沉静而缓,别人脉动四五十次,你方动一次,内含神气,当真是世上少有,是否练过何奇术?”
楚月儿道:“我与夫君都练过老子的吐纳奇术。”东皋公叹道:“怪不得,怪不得。如此脉象常人绝不能有。龙伯,老夫为你把一把脉象。”伍封的马车在铜车之前,此刻稍停,等铜车赶上来,将手伸入帐中,东皋公搭脉一时,惊得“咦哟”连声,气息渐粗,道:“这……,这真是从未见过!龙伯和月儿这脉象是老夫平生仅见,从脉象看来,你们神力无限,气脉旺盛而脱俗,周身浑元而不破,只能用‘神异’二字说出来!以此脉象,阴阳混成,邪不能侵,绝无伤病之虞!”楚月儿也为伍封搭脉良久,道:“月儿可不懂。”
伍封抽回手,马车在前行着,听见东皋公滔滔不绝地教楚月儿诸般医道,早已经不限于用毒解毒之法,心中一动,想:“莫非老先生看中了月儿,要将自己的医术教给她?”
楚月儿学了大概的的切脉之法后,东皋公道:“这么说法纯是虚谈,非得找人相试不可,你与龙伯的脉象绝非常人所有,不足为凭,须另找他人一试。”楚月儿笑道:“月儿正想试试。小兴儿,你将手伸过来。”
鲍兴乐道:“小人脑筋有时候不大灵光,每想寻医,今有两大神医在此,不可不让你们诊治。”他将马缰交给身旁的小红,大手伸入铜车帐中。
楚月儿和东皋公搭一会儿脉,东皋公道:“此脉寸实而关冲,这小兴儿身子壮实,力气不小,少有生病之时,不过他浑浑噩噩,一生快乐,甚是难得。”楚月儿也搭脉相试,道:“原来这叫作寸实关冲。”又小红将上来搭脉,东皋关轻轻一搭,笑道:“此脉可有趣。”楚月儿切脉一阵,道:“似是寸奇而关重,老先生,此脉是说些什么?”东皋公道:“这叫喜脉,原来这御者是名女子,已经怀孕四月了。”
鲍兴大喜,道:“嘿,小红终有了喜,哈哈!龙伯,这小孩儿要起个名字,还有,老商,日后这……”,他叽叽呱呱地东说一句,西扯一言,似乎片刻间这小孩儿便要生了一般。
伍封也是大喜,笑道:“还有六个月才生产,小兴儿可不用这么性急。雪儿,你将小红带到你们车上去,这粗重的活儿可不能让她做。”
商壶从后面赶上来,道:“老先生、姑姑,也替老商诊治瞧瞧。”也不怪东皋公是否愿意,将大手伸入帐中,楚月儿和东皋公切脉一试,楚月儿道:“这脉象又有不同,似乎有病象。”东皋公道:“这不是病象,是内伤之象。这位老商想是在七年之前,不对,是八年之前胸口被人击伤,并未医治,仗着身强而挺了下来,次年又伤了同处,不过这一次曾就医,医好了新伤,但旧伤却沉积下来,成为痼疾。”
商壶惊道:“咦,老先生真是神人!八年之前老商在楼烦被一个叫朱平漫的家伙打了一拳,次年与胡人练跤又摔伤了同处,医了二十天方好。”
楚月儿搭着其脉沉吟道:“老先生,这痼疾似乎难愈,是否有碍?”
东皋公道:“眼下虽不会发作,再过十二年,一发再不可治,非死不可!”
伍封与楚月儿大吃一惊,伍封忙道:“老先生,老商是月儿的爱徒,烦老先生诊治。”东皋公笑道:“无妨,幸亏老商遇到了老夫,否则再拖上数月,疾患入骨,神仙也难救。先停下车来,老夫用针为他止住内伤,每日施针,等到了城邑,再药石相攻,十数日便可以痊愈。”
伍封忙命大队停下来,在道旁少歇,东皋公一边替商壶扎针,一边指点楚月儿诸般针法及用途,道:“家师治病之方法有汤、熨、针、醪四法,汤即汤药,熨即药敷按摩,针即针灸,醪即药酒,这针法除进针出针外,又有捻转、提插、留针等手法,月儿仔细瞧着。”其实为商壶施针不过一会儿功夫,东皋公为楚月儿讲解用针却用了一个多时辰。
楚月儿问道:“老先生有如何能分出老商的旧伤是在七八年之前?”东皋公道:“从脉象便可得知,不过这需要
众人“噢”了一声,心忖这楚文王一心为了桃花夫人,虽然难得,却因女色而轻士卒,以致败亡,也是自寻其祸。
老者续道:“楚文王死后,桃花夫人长子嗣位,但这人只继了楚文王的酒色,但其父的武略丝毫也没有学到,在位三年,专事游猎,无一政施设,故而谥不称王,只称‘堵敖’。桃花夫人次子熊恽文才武略俱佳,向为桃花夫人所爱,又为国人推服。堵敖心忌其弟,常想杀之,左右多有为熊恽周旋者,以致反复不决。熊恽自不能免,索性暗蓄死士,乘堵敖出猎时袭而杀之,以病薨告知桃花夫人,桃花夫人心中虽疑,也不欲明白此事,否则仅余一子也难免,遂使诸大夫立熊恽为王,即楚成王是也。”
伍封道:“楚成王用子文为令尹,灭弦、黄、六、英、夔,楚境四扩,武攻强盛一时。”
老者道:“楚成王初立,以王叔子元为令尹。子元自其兄楚文王死后,常有篡立之心,又慕其嫂桃花夫人之美,欺楚成王年少,遂于王宫之旁大筑馆舍,每日歌舞奏乐,欲惑桃花夫人之心。桃花夫人听说是令尹子元的新馆,叹道:‘先王舞干戈以习武事,以征诸侯,是以四方朝贡不绝。如今令尹不图武事,而乐舞于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侍卫将桃花夫人之语转告子元,子元甚感惭愧,遂发兵车六百乘,亲自引着伐郑,但郑国防守甚严,子元无甚兵略,见无机可乘,连夜退兵。他不战而退,反让人先到桃花夫人处谎称得胜。桃花夫人怎会被人所骗?道:‘令尹大获全胜,当宣示国人,哪有这么鬼鬼祟祟跑到未亡人之处相告的?’子元大为惭愧。”
楚月儿笑道:“桃花夫人聪明得紧。子元想必会收敛心神,专心国事了吧?”
那老者摇了摇头,续道:“子元伐郑无功,内不自安,又想成了楚王,桃花夫人自然为他所得,是以篡谋甚急。后来桃花夫人略有小恙,子元假称问安,移寝具入宫,桃花夫人却使侍女执剑守户,子元不敢闯入,留在宫中三日不出,纠缠不休,让其家勇数百围住王宫。桃花夫人派人向子文告急,子文密奏楚成王,半夜袭破子元家勇,入宫杀了子元。到桃花夫人寝室前问安。次日楚成王升殿,灭了子元一家,其后才用子文为令尹,国事定而大治。桃花夫人故后,楚成王葬母于父冢,此地息侯所葬之处,楚成王遵母之嘱,在此处雕了这座桃花夫人之像,以慰息侯于九泉之下。”
伍封“嘿”了一声,赞道:“这桃花夫人其实不仅貌美,还通达明断,了不起!”楚月儿笑嘻嘻地道:“女子通达明断者不少,但美貌而通达明断者甚少,怪不得夫君赞她!”伍封笑道:“怎么月儿也学起公主的脾气来,总当为夫是个好色之徒?”想起妙公主的诸般顽皮,不禁微笑,心忖自己似乎也是个好色之徒,道:“我若见了桃花夫人,自然不会如子元之不堪,不过楚文王为一女而大兴杀伐,我未必做不出来。譬如田相若将月儿索要回去,我定会杀入田府以夺回来,诸事不顾。”
楚月儿格格笑道:“夫君多半做得出来,正如夫君所说,你这番狠劲也是非同小可!”伍封哈哈大笑,道:“哈哈,是么?”
众人听了这半天故事,甚有感触,伍封让鲍兴拿了五金给这老者,这五金即是百两黄金,老者推辞道:“老夫只是说几句话,何用如此厚赐?”
伍封笑道:“老先生这故事说得好听,足解在下等旅途之困乏,区区五金不算什么。”老者摇头道:“黄金之物老夫身上多得是,并无所用。”他说着话,随手从袖中拿出一把楚国常用的饼金来,放在地上,又从怀中摸了一把,赫然是数块宝玉。
众人想不到这老者随身携有许多金玉,心想他的大袖之内不知还有多少。楚月儿好奇道:“老先生原来十分富阔,夫君可看走眼了。”伍封道:“老先生谈吐非凡,想必是大有身份之人,未知能否相告名讳?”
老者微笑道:“老夫是扁鹊的弟子东皋公,与令尊曾有一面之缘。”伍封大惊,叩拜道:“原来是先父之大恩人,晚辈失敬了。”楚月儿等人也忙跪叩。
东皋公将伍封搀起来,又让楚月儿等人起身,道:“老夫是个闲散小人,隐居于此地久矣,龙伯和月公主如此大礼,老夫可担当不起,恐致折寿。老夫活了九十四岁,还想多活几年。”
这东皋公的确是伍子胥的恩人。当年伍子胥携公子胜(白公胜)东逃往吴,路过昭关,关上有楚兵把守,悬图刻形貌,无法通过,伍子胥大急之下,一夜白发。幸好他在关内林中遇到东皋公,东皋公见伍子胥身高一丈,形容极伟,遂请友人皇甫讷假扮伍子胥,皇甫讷身高九尺,又与伍子胥有些相像,东皋公用些药汤将伍子胥面容变色,取村家衣服给伍子胥和公子胜换上。黎明之时,皇甫讷故意慌慌张张地过关,被士卒当成伍子胥拿住,叫嚷吵闹之下,伍子胥和公子胜便混过了昭关。他头白变白,脸上易色,故意弯腰以掩其高,遂能过关。伍子胥过关许久,东皋公才拿着过关文牒到关上来,声称与皇甫讷相约过关东游,楚人验实,才知道捉错了人,陪罪放了,坚守昭关如故,却不知道伍子胥早已经混过了关去。
伍封向众人说起此事,道:“若非老先生援手,家父早晚亡于楚国,我也就生不出来了。是以老先生对我们一家有天大恩德。”
东皋公摇头道:“老夫倒不投你们报恩,老夫一生救人,从不杀人,只是见令尊是当世英雄,不忍他含冤而亡,才会偶施援手。今日老夫路过此地,被龙伯的从人请来,老夫恰好知道桃花夫人之事,才会向你们说一会儿话。”
伍封道:“先父多年来派人寻觅老先生和皇甫先生,可一直未能找到,未知皇甫先生在何处,晚辈想向他叩头致谢。”
东皋公摇头道:“十余年前,皇甫老弟入山采药,误入金夜花丛,中了花毒,老夫一时间寻不到解此毒之药,三日后皇甫老弟便死了。”
伍封叹了口气,觉得甚为遗憾。楚月儿点头道:“金夜花夜间开光,发金色之光,白昼看时,与寻常牵牛花相似。要解此毒,除了防风、甘草、桂枝之外,非得用一味雪昼草不可。此草在极北之地才有,楚国可寻不着。怪不得以老先生之能,也不能救到皇甫先生。”
东皋公大奇,惊道:“咦,原来月公主也懂得医道。虽数十年的医士也不易知道这雪昼草、金夜花,月公主竟能知道这两种奇物,解法也得当,委实高明!”
楚月儿笑道:“月儿可不知道,这是计然的竹简上写的,月儿记在心中,也不知道对不对。”
东皋公问道:“计然是个什么人?”楚月儿将计然之事简单说了一遍,道:“他那竹简月儿记在心中,可惜放在莱夷未曾带来。”
东皋公大感兴趣,道:“原来世上还有人专研用毒解毒之法,听来高明之极。既然你记得,大可以一一说给老夫听。”
楚月儿道:“是。譬如说用锡配天仙子,便可合成一味毒药,名叫‘惜见天’,此毒夜发,天光即死,要解此毒,便得用杏仁、黑豆、甘草,再用蓝子汁和盐水煮成药汤,便可以解毒了。”东皋公闭目沉吟,不住点头,道:“高明,高明。这一味盐水想得周到,老夫一时间便想不出来,不过若将蓝子汁改为绿豆汁,只怕更有解毒之效。”他是扁鹊的亲传弟子,医术自然要较计然高,楚月儿深信不疑,道:“简中有几种毒药都用绿豆以解,这绿豆汁自然是好。还有一毒,是用天南星配芫花、巴豆,三毒相合,十分厉害,要解此毒……”,东皋公沉吟道:“这三种都是剧毒之药,老夫若用生姜、黑豆混碾成粉,再加上大豆汁、黄莲汁、菖蒲水,以冷水调合服用,理应可解这三毒。”楚月儿点头道:“简上确是这么用法,不过多了一种干姜汁。”东皋公猛拍大腿道:“妙!这干姜汁用得极妙!药量如何?”楚月儿道:“常人用当然是生姜一两三钱、黑豆四两,大豆等各用五钱轧汁;若是肥胖之人,须得加些……”
他们一老一少说得十分高兴,伍封等人面面相觑,忍不住暗暗好笑,不敢打扰。楚月儿和东皋公越说越是兴奋,说了好一阵,东皋公睁眼道:“是了,老夫扯着月公主这么长篇大论,不免耽误了你们的行程。”
伍封忙道:“无妨,我们并无急事,大可以在此地设帐过夜。”东皋公笑道:“这如何使得?不如这么着,老夫随你们一路前往,途中正好于月公主研究些医术,一举两得。老夫许久未闻过高明的用药之术了。”
伍封道:“晚辈正有意请老先生到我成周的府上小住,同行更好。老先生是否还有家人?晚辈派人一并接来。”东皋公笑道:“老夫只身一人,行至何处便在何处落脚,何来家人?”
鲍兴将地上饼金捡起来交给东皋公,伍封命将铜车华盖上的锦帐放下来,楚月儿扶了东皋公上铜车安座,人车前行,东皋公却与楚月儿在铜车帐中滔滔不绝。便听东皋公道:“月公主,这……”,楚月儿道:“老先生唤我‘月儿’便是。”东皋公道:“是极,月儿,有一种蛇毒可十分厉害,名为乌头子,喜欢在川乌、草乌附近藏身,竹简上可有解法么?”楚月儿道:“似未见过解法,不过简上说蛇所在处,七步之内必有解药,那川乌、草乌是否可为解药?不过川乌有剧毒,可不敢用。”东皋公呵呵笑道:“正是用川乌来解,这叫作以毒攻毒。用草乌也可解之,不过川乌草乌不过混用,单用一味即可。”楚月儿问道:“为何不能混用?”东皋公道:“川乌草乌相配大有禁忌,合用则失去药效,此类禁忌之药有十九种,叫‘十九畏’;还有十八种药不能混配,否则便有大毒,足以致命,称为‘十八反’。用药者不可不知,老夫教你这歌诀,日后你用药时要谨记,另外,药剂使用分君臣佐使,不可不知。先背这‘十九畏’,歌诀是:‘硫磺原是火中精,朴硝一见便相争……’。”
伍封心忖这二人一个是九十四岁的白首老翁,一个是十七八岁的美貌少女,偏能说到一起去,兴趣昂然,也算是奇事一件,觉得甚为有趣。
一路上有东皋公相随,行程就慢了许多,虽然这世上有很多人被称为神医,但真正的神医,无过于扁鹊者。东皋公是扁鹊的弟子,从医八十余年,医道非同小可,世上再无第二人可以比拟,这些天他将用药的诸般法门禁忌效用一一说给楚月儿听,又时时停车,带楚月儿在道旁采药辨认,楚月儿对此道本有兴趣,用心记忆不提。
这日到了棠溪,还离城邑甚远,便见夫概带了数人在道旁等着。
伍封微觉愕然,将楚月儿从铜车上唤出来,带众女下车拜见夫概,伍封道:“舅爷爷可好。”夫概笑道:“还好,难得封儿有心,竟绕到此地来探我。不过老夫无甚颜面见人,不敢迎你入城。”
圉公阳和庖丁刀将一早准备好的一车礼物拿上来,夫概身后转上来一人接过,看那人时,正是上次见过的那力气惊人的庄战。
伍封忽想起上次在吴国时,小鹿绕道楚国买梁种,再赶到吴国,说过途中遇到了这庄战,还比试过刀剑,连小鹿也不敌此人。后来匆匆回齐,一路上多生变故,叶柔亡故,众人心情寥落,回齐之后又忙着送田燕儿成亲,一直未细问过小鹿与庄战交手的事。此刻见到此人,兴趣大生,不住地向庄战打量。
众人在道旁林间席地而坐,伍封让鲍兴请东皋公来,东皋公却不愿意见生人,伍封只好由得他在车上休息。夫概的从人奉上美酒瓜果供众人解热,夫概见伍封和楚月儿都注意这庄战,笑道:“封儿,小战力气不小,剑术又精,老夫对他甚为看重。上次瞒着老夫与令徒小鹿比试了一次,被老夫好一顿责怪。”
楚月儿看了庄战好半天,甚觉亲近,忽想起渠公到她族中挑选人才之事,她和伍封在鲁国为孔子吊丧,渠公将庄大等人带了去,还说族中有一人名战,素为族人推重,这人之名也是“战”,莫非就是此人?她道:“夫君,渠公曾说我族人之中有一人善剑术,名为战。”
伍封也想了起来,夫概笑道:“月公主猜得不错,小战便是你的堂侄,他常回族中去,是以你们族人都知道他。”
庄战道:“其实在上次见面时,小人便依稀认出了月公主。虽然说女大十八变,月公主长得高了,也更为美丽,但眉心那颗美人痣小人是认得的。月公主四岁时,小人正好回族中去,还抱过月公主。只是月公主嫁了龙伯,身份尊贵,小人可不敢相认,免得别人当小人是否趋炎附势之徒。”
楚月儿又惊又喜,道:“月儿可没有什么印象。”伍封笑道:“若非月儿想起来,小战是否还不想相认呢?”寻思:“小战与月儿姊弟果然关系不同,庄氏老一辈都认不出月儿,偏偏小战能认出,若非他以前对她们姊妹细心照顾,怎能认识?”
庄战道:“眼下月公主是楚国公主,龙伯又是天子之师,小人再要相认,岂非更加不成样子?是以央师父不要说出我的身份来。”
伍封佩服道:“原来小战是舅爷爷的徒儿,怪不得剑术能胜过小鹿儿。”
夫概摇头道:“小战的剑术胜过老夫多矣,可不是老夫教的。他尊老夫为师,是因为我教他冶铁铸剑之技,不过他往吴越楚国寻访名师学习铸艺,比老夫的铸艺要高明不少。”
伍封奇道:“小战的剑术能胜过小鹿儿,非剑术高手绝对教不出来,未知师从何人?”
庄战摇头道:“小人这套剑术是小时候用一条两头蛇与人交换来的。”伍封与楚月儿大吃一惊:“两头蛇?”伍封道:“那人想必是剑中圣人支离益的门下。”
庄战道:“十余年前,小人在林中见到一条长长的两头蛇,不知其厉害,用竹竿按住,正想将蛇打死,忽然林中转出一个人来。那人并未说过名字,不过他气派甚大,虽然他可以轻松将蛇夺了去,却不愿意有失身份,便要出金帛买走。小人说此蛇见者不吉,非打死不可,他劝了小人好半天,见小人不要金帛玉器,遂说要传授小人一套剑术,以换此蛇。小人自小对剑术便很感兴趣,便答应了他,他先将蛇装入竹篓,然后教了小人一套剑术。名为‘开山剑术’,说小人的力气甚大,正合用这套剑术。”
伍封心想这“开山剑术”除了自己懂得一些外,便只有支离益和朱平漫二人擅长,董门其他的人包括董梧在内都不习此套剑术,问道:“那人多大年纪,是何模样?”
庄战道:“那时他有四十余岁,眼下应该五十多岁了,生得十分高大,约有九尺,模样古朴。”楚月儿摇头道:“不是朱平漫。”伍封道:“董梧这人没有这么高大,说不定这人便是支离益。”
庄战练剑这么久,自然知道支离益的大名,又惊又喜,道:“他是剑中圣人支离益?!他甚有耐心,教了小人一个时辰,小人练会之后,他又用了两个时辰与小人拆招,指点每一招的用法,小人慢慢使给他看,他长叹了一声,说他有一个弟子也会这剑术,不过日后小人这套剑术练熟了,必定胜过他的弟子。”
伍封和楚月儿知道那人口中的弟子必是朱平漫,一头,道:“那人果然是支离益。”伍封笑道:“小战能得剑中圣人支离益亲授剑术,福气可不小,怪不得能胜过小鹿儿。”楚月儿道:“以小战的天资,支离益怎会轻易放过,不收为弟子呢?”
庄战道:“他也曾说过要收徒,不过小人不愿意离开楚国,是以未拜他为师,他只好带了那两头蛇离去。”
伍封问道:“如此良师天下间只有支离益一人,你为何不愿意随他去?”
庄战叹道:“当时小人才八九岁,怎知道面前的是天下奇人?何况二十九年前小人才四岁,随家父离开了族中,正值吴军伐楚,攻入郢地,国内大乱,家父抱着小人兄弟二人正逢乱兵,被撞得跌倒了,人群拥动,小人便与父兄失散。小人常想,父兄早晚会来找小人,是以不敢离开楚国去。”
夫概道:“老夫从吴国逃出来奔楚,被封在棠溪,一路过来,在途中见到小战乞讨。小战年方五岁,却甚有胆气,老夫便将他捡了回来收养,过了七八年才打听到他族人的下落,命他回去,不过他回去之后又赶回堂溪,他怕父兄回族中去,其后每过两三年便回族中一次。”
伍封叹道:“我在月儿族中时,族长说其二弟离族而去,原来就是小战的父亲,这真是巧得很。”
楚月儿道:“夫君,好不好我们再来个千金悬赏,为小战寻觅父兄?”伍封点头道:“如此甚好,只要知道小战父兄名讳,便好办了。”
庄战喜道:“家父带小人出来时,以庄为姓,家父名叫庄城,家兄……”,伍封和楚月儿愕然道:“庄城?!”
庄战惊道:“怎么?”楚月儿道:“成周梦王姬府上总管便叫庄城。”他说起庄城的样貌,庄战大喜,道:“那正是家父,想不到他老人家在成周。”
伍封叹道:“我一生遇到过巧事不少,尤以今日算是巧之有巧。”楚月儿笑道:“幸亏夫君心思一动,要来探望舅爷爷,这才搞清楚许多事。”
夫概呵呵笑道:“虽然小战不愿意,但老夫听说大王赐封儿之子为庄氏之长,赏赐邑地,今日本就想让小战与你们相认,然后为你们效力,也免得埋没了小战的剑术。想不到还有如此变故,这真是难得。小战,你们便随封儿去吧,日后也好见功。”
庄战道:“这虽然是好,不过小人要问问家父的意思,这便随了龙伯和月公主去,先拜见父兄再说。”
伍封道:“如此甚好,令尊便会答应。”又皱起眉头,道:“小战,有一事你先得心中有数,令尊说其二子一女均已经亡故,想是当你已经亡于乱中。不过令兄只怕已经不在世上了,他有一子名曰庄周,随令尊在一起。想来是令兄与令尊在一起,长大后娶妻生子,早些年亡故。”
庄战怔了怔,眼中微微湿润,叹道:“其实小人心中早有了准备,只是不敢细想而已。”
夫概叹道:“伍氏一家与吴王有仇,幸亏封儿不记旧怨,以吴民和宗祀为重,两番败越,却被夫差加害,老夫也甚为有愧。小战自小随我长大,剑术也高,老让小战投于封儿府上,也算是报答封儿。如今小战已经得知父亲的下落,老夫的心愿已了。小战,你与封儿和月公主是亲人,今后当尽力报效,不可懈怠。”
庄战点头道:“如果家父愿意让小人投入龙伯府上,我便尽力而为。”伍封皱眉道:“小战怎不叫我们为姑姑、姑丈,非要称‘月公主’、‘龙伯’这么见外?”
庄战摇头道:“龙伯手下臣属众多,当着这么多人,自然当叫‘龙伯’、‘公主’,免得别人以为小人仗着是亲戚,打着你们的旗号来唬人。何况家父是月公主的父亲的堂侄,小人与月公主之间的亲戚关系可有些疏远了。”
楚月儿不悦道:“都是一族之人,亲疏哪用分得那么细?”庄战道:“家国都有其规矩,可不能乱套。眼下小人还不是龙伯和月公主的臣属,非得这么叫不可。”
伍封与楚月儿见他颇有些迂腐,苦笑摇头,心忖夫概并不怎么守礼,否则便不会有自立吴王之事,想不到他这弟子却将谦躬守礼之极。当下引庄战见过鲍兴等人,又让庄战回城收拾行囊。
众人谈了许久,等庄战拿了个小行囊来,楚月儿见他只身一人,问道:“小战还未成亲么?”庄战道:“未得家父之命,怎敢私下成亲?”
夫概怕耽误了伍封的路程,命从人将准备好的礼物拿上来,那是十口铁剑。夫概起身告辞,众人互道珍重,伍封一众带着庄战继续北上。
东皋公在车上苦候了楚月儿这么久,急不可耐,此刻楚月儿才上车,东皋公便道:“月儿,你可知有的毒药服上,从外表可看不出来,待外征象出来褒时,已经不能救了。你又用何法知道他是否中毒,所中何毒?”
楚月儿道:“这个月儿便不知道了。”东皋公笑道:“我告诉你这法子,医道所谓望闻问切,用此四法便知。老夫先教你这‘切’法,切分脉诊和触诊,脉诊即是切脉象,人之脉象常见的二十八种,如浮、沉、迟、缓等等,你看这腕上,此处曰‘寸’,此处曰‘关’,此处曰‘尺’,手指这么搭上去,便知……,咦!月儿,你这脉象古怪,沉静而缓,别人脉动四五十次,你方动一次,内含神气,当真是世上少有,是否练过何奇术?”
楚月儿道:“我与夫君都练过老子的吐纳奇术。”东皋公叹道:“怪不得,怪不得。如此脉象常人绝不能有。龙伯,老夫为你把一把脉象。”伍封的马车在铜车之前,此刻稍停,等铜车赶上来,将手伸入帐中,东皋公搭脉一时,惊得“咦哟”连声,气息渐粗,道:“这……,这真是从未见过!龙伯和月儿这脉象是老夫平生仅见,从脉象看来,你们神力无限,气脉旺盛而脱俗,周身浑元而不破,只能用‘神异’二字说出来!以此脉象,阴阳混成,邪不能侵,绝无伤病之虞!”楚月儿也为伍封搭脉良久,道:“月儿可不懂。”
伍封抽回手,马车在前行着,听见东皋公滔滔不绝地教楚月儿诸般医道,早已经不限于用毒解毒之法,心中一动,想:“莫非老先生看中了月儿,要将自己的医术教给她?”
楚月儿学了大概的的切脉之法后,东皋公道:“这么说法纯是虚谈,非得找人相试不可,你与龙伯的脉象绝非常人所有,不足为凭,须另找他人一试。”楚月儿笑道:“月儿正想试试。小兴儿,你将手伸过来。”
鲍兴乐道:“小人脑筋有时候不大灵光,每想寻医,今有两大神医在此,不可不让你们诊治。”他将马缰交给身旁的小红,大手伸入铜车帐中。
楚月儿和东皋公搭一会儿脉,东皋公道:“此脉寸实而关冲,这小兴儿身子壮实,力气不小,少有生病之时,不过他浑浑噩噩,一生快乐,甚是难得。”楚月儿也搭脉相试,道:“原来这叫作寸实关冲。”又小红将上来搭脉,东皋关轻轻一搭,笑道:“此脉可有趣。”楚月儿切脉一阵,道:“似是寸奇而关重,老先生,此脉是说些什么?”东皋公道:“这叫喜脉,原来这御者是名女子,已经怀孕四月了。”
鲍兴大喜,道:“嘿,小红终有了喜,哈哈!龙伯,这小孩儿要起个名字,还有,老商,日后这……”,他叽叽呱呱地东说一句,西扯一言,似乎片刻间这小孩儿便要生了一般。
伍封也是大喜,笑道:“还有六个月才生产,小兴儿可不用这么性急。雪儿,你将小红带到你们车上去,这粗重的活儿可不能让她做。”
商壶从后面赶上来,道:“老先生、姑姑,也替老商诊治瞧瞧。”也不怪东皋公是否愿意,将大手伸入帐中,楚月儿和东皋公切脉一试,楚月儿道:“这脉象又有不同,似乎有病象。”东皋公道:“这不是病象,是内伤之象。这位老商想是在七年之前,不对,是八年之前胸口被人击伤,并未医治,仗着身强而挺了下来,次年又伤了同处,不过这一次曾就医,医好了新伤,但旧伤却沉积下来,成为痼疾。”
商壶惊道:“咦,老先生真是神人!八年之前老商在楼烦被一个叫朱平漫的家伙打了一拳,次年与胡人练跤又摔伤了同处,医了二十天方好。”
楚月儿搭着其脉沉吟道:“老先生,这痼疾似乎难愈,是否有碍?”
东皋公道:“眼下虽不会发作,再过十二年,一发再不可治,非死不可!”
伍封与楚月儿大吃一惊,伍封忙道:“老先生,老商是月儿的爱徒,烦老先生诊治。”东皋公笑道:“无妨,幸亏老商遇到了老夫,否则再拖上数月,疾患入骨,神仙也难救。先停下车来,老夫用针为他止住内伤,每日施针,等到了城邑,再药石相攻,十数日便可以痊愈。”
伍封忙命大队停下来,在道旁少歇,东皋公一边替商壶扎针,一边指点楚月儿诸般针法及用途,道:“家师治病之方法有汤、熨、针、醪四法,汤即汤药,熨即药敷按摩,针即针灸,醪即药酒,这针法除进针出针外,又有捻转、提插、留针等手法,月儿仔细瞧着。”其实为商壶施针不过一会儿功夫,东皋公为楚月儿讲解用针却用了一个多时辰。
楚月儿问道:“老先生有如何能分出老商的旧伤是在七八年之前?”东皋公道:“从脉象便可得知,不过这需要